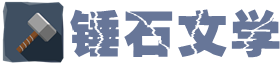铁屋中的呐喊 免费阅读 第11章 革命前夜
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联文学的知识,必定增强了他的论辩力和政治思想信仰。但是这些知识是否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却还难说。在他越来越相信俄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社会这样一个布尔什维克故事的同时,他却决不能看到在自己的国家也将出现这样的社会。从1927年开始,他已经觉得中国当时“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同时也警觉到“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卷3,第547页)虽然在政治思想上是指向未来的,但即使是在左翼年代,他也不愿把希望只放在未来。相反,他更重视这革命前夜的黑暗的现在。正如他向冯雪峰吐露的:
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样去想过。倘说是怎么样才能到达那将来,我是认为要更看重现在;无论现在怎么黑暗,却不想离开……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到将来再说,现在总须先改革。
他所面对的1931年以后的“现在”当然是黑暗的。随着抗日的浪潮,国民党政府的加紧审查,对左翼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左翼阵营本身的分裂和叛变,鲁迅在决心献身于革命文学的过程中进入了他一生中一个极困难的时期。
一
外界的环境是如此恶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对他不利。他过去一直比较健康,很少卧病和去医院。但从日记上可以看出,1932年他开始多病了。1933年9月给曹聚仁的信中说:“近年以来,眼已花,连书亦不能多看,此于专用眼睛如我辈者,实为大害,真令人有退步而至于无用之惧。”(卷12,第219页)在1933年稍健康些,到1934年年末病又更厉害起来了。这最后几年鲁迅似乎是被灾祸的阴影所缠绕着。和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政治思想的热情相对比,他的私人通信中却充满着抑郁的凋子,也苦于外界环境对他工作效率的干扰。1933年给姚克的信中说:“我自己是无事忙,并不怎样闲游,而一无成绩,盖‘打杂’之害也,此种情境,倘在上海,恐不易改,但又无别处可去。”(卷12,第297页)同年在给黎烈文的信中,表示了由于审查以及考虑到黎烈文的处境不得不婉约其辞的遗憾和歉意:
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骾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唯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
鲁迅所说并不完全是谦虚。他为《申报·自由淡》所写那些文章(后搜集在《伪自由书》中),确实比较“荏弱”。除了避忌审查的原因之外,他可能还苦于已怀疑自己的文学创作才能。
虽然他雄辩地用政治需要为自己的杂文辩护,但在1932年他仍说过自己或许缺少文学才能。他还进而承认由于自己缺少伟大的才能和外国语的学力,因而未能搞长篇的创作和翻译。(卷4,第184页)这些话正好和他为“匕首和投枪”式杂文辩护的公开的文章以及大量译文形成对比。1933年为自己的短篇小说选所作的序也是谦虚的: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卷7,第390页)
这意思在同年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就说得更坦率了:“学术文章要参考书,小说也须能往各处走动,考察,但现在我所处的境遇,都不能。”(卷12,第207页)在1934年他又写:“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卷5,第476页)
但正是在这生命的最后年月他的写作数量却提高到一个新的高潮。他的十六卷杂文中至少有一半是在最后四五年间写的,另外还有十多本译文。也可以说,这是他的战斗精神复活的一个标志,这精神是对周围环境压迫的反应:从敌人来的压迫越厉害,他的战斗精神也越猛烈。但是他作品的数量和猛烈的程度似乎也含有一种绝望的调子,似乎他已预感到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难以完成他要做的所有的事情了。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当他因病躺在藤椅上休息的时候,常感到正在面临死亡,不得不焦心于那些应做的工作:写文章,翻译,木刻,印行书籍等。1936年9月,即逝世前一个月,他曾在《死》中写过:“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卷6,第610页)
这种个人生命限期将至的感觉,还伴随着一种时代的终末感。在1934年、1935年间他曾多次将当前的时代和明末相比。如1935年给郑振铎的信中,就曾谈到现时文人的凶悍阴险和奴颜婢膝,和明代士大夫惊人地相像。(卷13,第11页)他写明末的一篇文章被审查掉了。但是蒋介石与日本人的调情以及反对抗日的情绪,却使他在这同一问题上发出悲愤的声音: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卷13,第52页)
1935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所作的序言中,还把自己的言论比作“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的事”。(卷6,第217页)
虽然正走向他的时代的终末和生命的迟暮,鲁迅仍不屈不挠,拒绝承认失败。他向萧军说过:“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不过这是暂时的愤慨,结果大约还是这样的干下去,到真的干不来了的时候。”(卷13,第52页)看来,面对极大的压力和阻碍去做某些事,正是鲁迅的一种嗜好。这种承担责任的悲剧景象,这种在并无充分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却愤怒地将自己投入工作的景象,是鲁迅精神的一个特殊方面,是既非他的批评者也非奉承他的那些弟子所理解的。批评者的不理解他可以无所谓,但这在他和他的弟子们的关系中却是重要的事情。
二
除了写作和翻译以外,耗费了鲁迅许多时间和精力的,是对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帮助。他和所谓文学青年的关系是包含甚广的,复杂的,甚至意义含混的。虽然他在晚年对青年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乐观,看来似乎更敏感,更注意自己,和青年并不那么融洽无间,并且已经公开宣布从进化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从来也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信心。从他给青年作家的无数信件以及他们讲述的关于他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渴望帮助青年也是他自己的需要的一部分。在这些“文学青年”做到了能让他倾听他们的话以后不久,他那平时的导师尊严的一面就被丢在一边,出现了一位非常和善和热心的人。和他对自己创造力的怀疑以及生命即将终止的不安感情联系起来看,这种对青年的需要透露了某些比认识上的热忱更深刻的内心的东西。我相信他对青年(特别是那些关系密切的弟子)的态度以及和他们的关系透露出他“心理”的某些内涵,是这一时期他的自我形象的核心。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对鲁迅那种父亲般的慈爱做了温暖的记录,书中充满了鲁迅爱心表现的细节。萧军近年出版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也揭示了这方面的情况,其中有五十三封鲁迅的信和萧军本人的注释。把这两本书和其他类似的回忆录结合起来读,使我们能够一瞥鲁迅在上海时的生活脉络以及他与青年作家相交往中的问题。
二萧和鲁迅相识相处的情况似乎是典型的。首先是他们抵达上海之前(1934年10月)在朋友们的建议下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立即复了信,答应读他们的作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两本书后来都经鲁迅审阅后发表了,现在海外也流行着)。他们和大师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1月27日,是由鲁迅谨慎地安排的(可能是为防备国民党警特)。他们在指定的地点来到内山书店,然后隔着几步路远近尾随鲁迅到一个俄国咖啡馆,坐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如萧军后来回忆的,在政府警惕的监视下,上海左翼作家当时过着不正常的生活,除了“工作和组织关系”,极少社会生活,他们很少交换真名或真地址,往往在茶馆或街头秘密约会。在这种环境中,鲁迅仍以邀请吃饭的方式给二萧介绍了一批左翼青年作家(用信邀请,为避免邮检,常用各种借口,地点也不确写)。他还赠钱给他们,鼓励他们写作,帮助修改他们的作品,为他们找各种渠道发表。他甚至对萧红衣着的颜色和式样也关心。这样,两位新作家(以及其他新作家)对鲁迅的衷心感戴和敬佩也就自然建立了。
可能是由于鲁迅对这两位文坛新人寄予了一种特别的父亲似的关注,他一再在给二萧的信中警告说:“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但他对这两个青年人的保护也是自己态度的另一方面的反映,即多疑,不信,如夏济安所说,有一种对“小刺和枝桠”的病态的敏感,把它们“夸大成大树,恶意地砍削和打击”。夏济安在关于鲁迅和左联解散问题的论文中,还有如下的分析:
他在上海的生活,虽然也常参加一些聚会和看电影(如其日记所记),但这些事对原是这么阴沉的心却未能使之愉悦和轻松,也未能移去他所手植的对付臆想的或真正的敌人的自卫心理的樊篱。他自己也未能从迫害狂中解放出来,其病状是从他的写作中表现出来的。
如果说在他早期作品中已经闪现了一定程度的迫害狂,在现在的环境中就更扩大了。在上海租界的庇护下可以避免被捕,但却逃不开谣言和其他方式的威胁。威胁的来源部分来自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在1934年11月12日给二萧的信中,他承认“压迫的,因为他们并不统一,所以办法各处不同,上海较宽”。威胁的另一来源是一些小报和文学刊物,上面有由一些自称作家的“坏人”炮制出来的各种谣言。这些人有的可能是国民党雇佣的,有的是当年的左翼现已“转向”者。正是这种现象,刺激鲁迅使他说出如下的苦恼: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蛆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这极能说明问题的一段话,摘自对二萧一封信的回信。二萧的信写于1934年他们第一次会面后不久。这两个年轻人因看到鲁迅病后的身体状况而感到难过,如萧军所回忆的:“两颊深陷,脸色是一片苍青而又近于枯黄和灰败,更突出的是先生那一双特大的鼻孔,可能是由于常常深夜不眠或者吸烟过多竟变成了黑色!”鲁迅在复信中把这归之于人到五十岁以后的自然现象,人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如上面所引的段落所示,他的来日无多以及才能有限的感觉,是和因内部的背叛而激起的孤独感有关的。因此,他对这天真的、未被腐蚀的一对的真心关怀,也正透露出他内心感情的伤痕。他越是感到孤独,越是需要如二萧所体现的青年的天真无邪。
但这种心理要求并未完全得到满足。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一书中有一整章是回忆鲁迅和青年们的交往的。他常常受挫。有些青年人利用鲁迅的好心为自己求名或找职业,在这之前或之后不无反咬一口的举动。鲁迅和他们初见面时看来高傲疑心,固然部分地是“讽刺”的性格使然,但也是必要的“对付臆想的或真正的敌人而手植的自卫的樊篱”。作为长期经验的结果,这也包括青年在内。但是,当一个青年作家终于获得他的信任以后,他外貌的一层冷冰也终会融化。这从他和许广平的“情书”中看得最清楚。许广平是他的学生,几乎年轻二十岁,最初给老师写信是谈共同有兴趣的一些认识问题,最后终于两心相近。从《两地书》中可以看出,在长达五年的恋爱过程中(1925—1929年),她是积极地追求,而鲁迅是逐渐放松了自己的防卫,最后终于向她袒露自己最黑暗的思想。他们的同居生活,在鲁迅一生和青年关系的故事中,应说是最幸福的一章。
除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许广平外,鲁迅在上海时最亲密的弟子是柔石和冯雪峰。柔石打动了鲁迅是因为他的纯真和宁静的为人。在与创造社、太阳社最初协定组织左联时,柔石和冯雪峰都明显的是“鲁迅阵营”的人。但是,给鲁迅以巨大震动和悲哀的,是柔石和其他四烈士一起,最先被国民党杀害了。失去柔石以后,冯雪峰在许多方面都是鲁迅的第一名弟子。出版于1952年的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冯雪峰和鲁迅同乡,都是浙江人。最初是由柔石于1928年12月介绍给鲁迅的。1925年至1926年在北京时他曾听过鲁迅几次讲课,当时的印象并不很好,觉得他太冷,蔑视一切,而且“对一切人都怀有疑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是一个矛盾的、难于接近的人。这是一个在外者的并不全错的评价。但是,在他开始了解鲁迅以后,原来的疑虑和偏见就都清除了。像柔石一样,他觉得鲁迅对他,以及对一切好青年,就像父亲一样。在他们认识的第一年,虽然鲁迅可能和柔石的个人关系更亲密,但谈论思想却和冯雪峰谈得更多,“大概因为我喜欢提到社会意识和文艺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鲁迅先生那时候最喜欢谈的”。当冯雪峰在鲁迅家附近觅得一个住处时,他的来访愈是频繁了,两人经常谈到深夜。许广平形容冯雪峰是“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很活动,也很用功”。冯雪峰自己也说他在鲁迅面前说话毫无拘束,甚至批评鲁迅在《野草》中的思想。
虽然鲁迅开始并不知道冯雪峰是共产党员,他们从1930年至1933年一直在左联工作中密切合作。在这问题上他们的师生关系似乎微妙地倒转过来了:冯雪峰好像不再是一个向大师求教的谦卑的学生,由于他在左联党的核心中的地位,慢慢地领导着了。他在数日以后整理了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鲁迅的讲话是没有草稿的,当时也没有记录,因此,其中冯雪峰的“贡献”一定相当可观。有趣的是,据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和冯的友人们最近所说,冯做这种润色部分地是由于有些青年成员在会后明显地表现失望,埋怨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
在1931年至1932年和“第三种人”论争时,冯雪峰编了鲁迅的两篇重要文章,做了校对,并且增加了一些他认为在策略上需要的字句。或许是出于妒羡这位心爱的学生占去了鲁迅那么多的时间,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详细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他怎样为左联的刊物纠缠着鲁迅,连次要问题也不放过,要求他做这做那,在讨论中寸步不让,直到说服了这位老师为止。这就剥夺了鲁迅非常需要的睡眠和休息。但是鲁迅仍然喜欢和称赞他。当然冯雪峰的意见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他本人也是在政治教条下艰苦工作的,但许广平述说的这些情况却完全证明鲁迅很喜爱冯雪峰,而且在他健康状况变坏的1936年,是依靠着这位有力的学生的。鲁迅对这位并不和他妥协的学生的温馨的感情,和他对那些臆想的或真正的敌人的严厉恰成对比。这种沉浸于极少数亲密者的性情恐怕不能只从政治思想的因素解释,这里还有晚年的心理因素在内。
在冯雪峰的回忆中,鲁迅的情绪经常起伏不定,但在1929年至1933年那段时期,总的说来都比前此和后此更愉快。冯雪峰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他当时热情洋溢地参加了左联工作。我想,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有其原因。1929年,鲁迅在四十八岁第一次做了父亲,第一次得以享受一个幸福的、巩固的家庭所提供的正常人应得的幸福。从许广平的回忆看,鲁迅是极其热忱地克尽父职,对孩子无微不至地爱护,喂食、洗浴、换尿片都要亲自参与,还按旧诗的平仄即兴吟出催眠曲哄孩子睡觉。鲁迅日记中经常记着带孩子去医院。在给他母亲的信中经常谈到海婴的健康和顽皮。他的父爱由于晚来似乎是过多了。因此,推测鲁迅是想把自己的父爱引申到他所有的“孩子”,即他的学生们,是不无理由的。于是,萧军、萧红、柔石,特别是冯雪峰,就成为这位大师温暖的父爱的受惠者了。正如萧军所说,他们为鲁迅所爱是因为体现了鲁迅已经少有的青年人的“稚气和不安定”。
再者,鲁迅在投身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的同时,他的思想也更因阶级和年龄的关系变得复杂了。他至少比他的革命同事们大十至二十岁,自觉属于前一代人。在他试着和苏联新的文学潮流同步前进时,也愿意和青年的左联领袖同步。瞿秋白和冯雪峰就是他所希望同步的主要人物。1931年,鲁迅和瞿秋白成为朋友,他非常欣赏瞿秋白的文学才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他们两人的思想关系已经有人做过充分研究。不过鲁迅把瞿秋白是看作可敬的朋友和同事,而不是学生。相比之下,鲁迅和冯雪峰认识较早,交往的时间也较长,在左联中也有一段相当长时期亲密合作的关系。冯雪峰虽然有些固执并颇为咄咄逼人,但自有其引入的魅力,不但对鲁迅,对另一些左翼作家也是如此。
但是,冯雪峰和瞿秋白于1933年、1934年相继离开上海去了瑞金。此时鲁迅的情绪骤然低落。他失去了非常珍贵的思想上的同伴,这是许广平所不能弥补的。这种空虚后来更痛苦了,因为传来了瞿秋白被杀的消息,鲁迅又一次承受了如柔石先自己而去的那种心情。接着是他的朋友,同是民权保障同盟参加者的杨铨的被暗杀。谣传鲁迅也是特务准备暗杀的目标之一。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时最大的问题却是来自左翼作家内部。
由于冯雪峰和瞿秋白离开上海,鲁迅也失去了很好的和共产党及左联的联系人。新的左联领导人是鲁迅所不喜的、称之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周扬在近期的回忆文章中也承认当时对鲁迅尊重不够。新和鲁迅联系的人是徐懋庸,他既是尊奉周扬们意见的,又是1936年决裂前鲁迅的追随者。据徐懋庸近期的回忆录,鲁迅当时不仅不为周扬们所尊重,而且还要求他按月给左联刊物以经济补贴。鲁迅尽了他的责任,但也不无怨气。代沟有很大关系。从徐懋庸回忆的一次谈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当时的情绪,这是在1934年6月9日:
只要是大家(指“左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我都赞成。要我做些什么,我当尽力去做。我有意见,以前都直白地提出,今后也一样。至于大家是否采纳,则又作别论。
出于对组织统一的尊重,鲁迅没有做公开的冲突,但是在个人通信中却压不住愤怒。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的信中说:
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是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卷13,第211页)
虽然左联内部的宗派斗争,至今还未完全弄清,但可以确定的是,鲁迅内心的郁愤终于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中爆发了出来。本来就有问题的关系,由于胡风的介入和冯雪峰的返回而进一步恶化。
关于鲁迅和胡风的关系,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第一手材料。虽然胡风被广泛承认为鲁迅晚年的第一大弟子,但胡风进入鲁迅的内部圈子不早于1934年。他虽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和激进的革命活动(在日本即因激进活动被驱逐),但据许多人的议论,却是个尖刻、会玩手腕、有权力欲的人,不仅不为周扬集团所喜,茅盾也不喜欢他。在左联内,大概只有冯雪峰是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可能就是冯雪峰把他介绍给鲁迅的。
冯雪峰和周扬集团的关系显然是不好的。1935年又因胡风对周扬关于典型人物的解释提出异议,使两方的关系更加疏远。据Kane的研究,胡风其实是在周扬等警告鲁迅他可能是奸细以后才成为鲁迅圈子里一个密友的,这是在1934年秋。此事引起了很坏的后果,鲁迅关于他和“四条汉子”会面的那段描写是众所周知的(卷6,第534—535页)。这段文字生动地说明了鲁迅对周扬等四人的极度反感。他所说的“一律洋服,态度轩昂”使人想起他给创造社人所加的著名的“才子加流氓”的外号。
事实上穆木天就是原来创造社的一个成员。在此,鲁迅对过去论敌的恨意和对左翼而又“转向”者的猜疑结合在一起,达到一种厌恶的感情,从而凡他们所攻击的人他反而觉得恰恰是好的。因此,他认为胡风尽管有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却正因为周扬们反对他,“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卷6,第535页)显然,鲁迅在这位新的学生身上(且不论他看得是否对)也看出了萧军、萧红以及冯雪峰的那种勇往直前的纯真,这是未曾在别的“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青年中找到的。
1936年4月冯雪峰回到上海,任务是寻找上海的地下党,使其和中央接上关系。到达上海后他立即去看鲁迅,却发现这位老人牢骚很大,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这是冯雪峰写在《回忆鲁迅》中的。后来据冯雪峰说,他写“回忆”的时候是有意把口号写缓和了的。实际上鲁迅说的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由于事先冯雪峰并不了解鲁迅和周扬们之间的不愉快,他当时很诧异。他在鲁迅家住了两个星期,没有立即和周扬接触,显然,个人感情更胜于组织的责任。
此时,对于1936年夏天爆发起的论战,两方面的人们都已经有所准备。其中的理论问题和政治背景已经有许多研究者做了分析。周扬等提倡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基于策略的考虑产生的,是一个响亮的反映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口号。鲁迅最初对“国防”这个主题并无反感,认为应当强调抗日,左翼应当广泛团结其他作家。但是当周扬等人在5月间决定把这一口号作为主要口号,并且专断地决定解散左联,另组“文艺家协会”的时候,对立就加深了。这种做法立即就使鲁迅集团有所反应。按冯雪峰近期的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由胡风和冯雪峰拟定的,意在维护左翼作家的阶级立场和革命性。鲁迅当时已在病中,同意了他们两人的建议。他们决定由胡风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个新的口号。这篇文章在5月末发表,于是开始了双方的论战。不过,冯雪峰还是尽力缓和矛盾,不使趋于极端,显然没有成功(只说服了胡风不要再写文章)。相反,在8月初,由于徐懋庸的信,情况更加恶化。这封信措词虽有礼貌,内容却甚高傲。他警告鲁迅应注意胡风之“诈”,尤其致命的错误是:他指出鲁迅错误的“根由”是“不看事而只看人”。
这种对鲁迅的判断力的批评触及了他的痛处。鲁迅写了长篇反驳,《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可能由冯雪峰起草(他已为鲁迅做过两次同样工作),由鲁迅再做修改。但文章第二部分给予“四条汉子”和徐懋庸的猛击却必然出于鲁迅自己的手笔。因为那种使他在政治上承担责任的道德热情必然也会支配他对年轻一代的态度。当在不可控制的盛怒之下走向极端时(当时情况必定正是如此),很自然地就划分了两类人:一类是可以信任的友人和学生,另一类是狡猾可恶的对手和转向者。鲁迅对人的观察本来常是敏锐的,盛怒却给这种观察力投下了暗影。
从鲁迅的暴怒,也可以感到他在青年中寻找可信任者的挫折感。徐懋庸和他通过许多信,寻求他的帮助,他也乐于帮助。最后却收到徐懋庸这样一封并不赞成他的信,认为一定是出于周扬等人的示意。因此,在他刻毒的回信中表现出一种被背叛了的怒气。他甚至走得这样远,最后还给徐一个通知,表示今后断绝一切来往。
除了个人因素外,鲁迅更因左联被专断地解散而受到打击。据徐懋庸和茅盾近期发表的回忆录,解散左联一事至少和鲁迅商量过四次。他先是不同意,后来意见有所缓和,出于他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他提出一个条件,即在左联解散时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以免被视为对国民党的投降。但当这个“妥协”的条件也被忽视以后,鲁迅的忿怒就压不住了。所以,在“两个口号”和解散左联这两个问题中,后者较前者给予鲁迅的伤害更大,因为左联实际上是象征着他献身于革命和献身于青年的结晶。在他参加的团体中,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据徐懋庸的回忆录,鲁迅1930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说到:“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左联解散这一击,不仅是打在他的政治立场上,同时也打在他长期以来俯首为青年服务的爱心上。
冯雪峰回忆说:他们于1936年两年离别后第一次见面时,鲁迅听他兴奋地谈着关于红区的、共产党的,以及长征等许多事情时,曾自嘲地说:“我可真的要落伍了。……”冯雪峰当时并不理解这感慨后面是什么意思,但是看来这位老人是反讽地说出了真实:他在多年的努力后,确实落后于革命了。冯雪峰承认鲁迅显然并不大了解长征后延安的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政策。
他在《回忆鲁迅》中所说的鲁迅思想上的“新的发展征象”以及向中国共产党“更靠近一步”的努力,应当说只是日后的合理的推想。因为,由于疾病和年龄,鲁迅这时又退回到早期回忆式的写作了,而且他已经想到了死。有趣的是,当他把《死》的手稿给冯雪峰看时,这位学生曾要求他做了两处修改,而且在此之前,还批评了他用“我”这个单数代名词太多,应当多用更有革命性的“我们”。
三
前面谈到的鲁迅和他的一些弟子的关系,以及他和周扬集团最后破裂的一些内部纠纷,说明一个明显的问题:鲁迅为左翼文学阵线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巨大努力,是基于他对文学青年的一种父爱态度,而这种态度,是并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回报的。在他的文章、诗、信件中,可以看到他这种感情的反复表现。例如他反对把翻译视为“媒婆”而以为像父母。他从事这种繁重的工作,是因为感到中国青年只是被很坏的粗粮所填喂,因此他想输入一些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的“精神的粮食”来给青年以营养。(卷5,第278页)在《自嘲》诗中,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
他还引申了这个“牛”的比喻,表示只要人们需要,他总愿意为他耕一耕田,如果受伤,他“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卷12,第185页)但是这个比喻还没有谈到另一种可能,即如果他甘愿为之服务的“孺子”并不纯真,他们是在通过欺骗和耍手腕损害他而建立自己的权力堡垒和影响,那么,他就不得不仅在私人信件上“呻吟”,最终竟如在1936年那样地大声吼叫了。
从较大的意义上说,这种父亲似的感情也可以说是1919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那著名的一段话的回响: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卷1,第130页)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作为一个父亲形象和在中国那种窒息人的“铁屋子”文化和社会中的孤独的清醒者,鲁迅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充当一座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如夏济安所说的中国传统故事中的那个大力士一样,坚持掮住城头已经落下的闸门,让他那些一同造反的伙伴们从闸门下面逃出去。这故事的革命意义是在于:这掮住闸门的巨人和逃出去的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叛逆者。
鲁迅在“五四”时期是文化的叛逆者,后来在三十年代转化为革命者。但是根本的感情是悲剧的,“因为,即使对一位巨人来说,那闸门也太重了,他终于被砸死了”。
鲁迅在晚年发现自己掮着的是双重的闸门,他解决了面对革命阵营以外的黑暗势力的问题,但似乎并未解决在那阵营以内的问题。如果像他过去那段具有进化论意义的话中所表示的那样,他的努力可以引导孩子们走向光明的未来,那么,他是极愿意掮住那双重的黑暗闸门的。
延安这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或许确实提供了他所说的“宽阔光明的地方”的可能,他自己却显然并未看到那实现的希望。如他在1936年对冯雪峰所说的:“但我,老实说,也没有去想过敌人什么时候会失败的事情。就只觉得这样和他(敌人)扭打下去就是了,没有去想过扭打到哪一天为止的问题。”这是非常坦白的心态的表露,说明胜利的景象对鲁迅来说并非指日可待,却要求长期的斗争。这斗争的过程本身确定了革命存在的意义。
既然革命是极长期的,就使鲁迅的父爱染上了强烈的牺牲色彩。全部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感情似乎都切近于牺牲和殉道的主题。鲁迅经常让读者(也让他自己)想到:由于他的年龄和经历,他只是一个老一代的人。他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也使他明白了自己不属于上升的无产阶级而属于别一阶级,是注定要消亡的。最后,他对时间的悲剧感,即意识到生活在一个未可知的黎明前的长期暗夜之感,更给他确定了父亲——殉道者这一角色的地位。
作为一个文学主题,牺牲主题似乎是贯穿于鲁迅的全部作品的。在1903年写的诗里就有“我以我血荐轩辕”;接着,在小说《药》和散文诗两篇《复仇》里,都有隐喻牺牲的形象。在晚年,他有时仍用牺牲的艺术形象喊出政治的忿怒,如得知柔石牺牲的消息时,他选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刊出,画上表现的是个母亲悲哀地献出了她的儿子。由于艺术的和“精神的”原因,他也非常喜欢麦绥莱尔的木刻《一个人的受难》,在解释中鲁迅说:“在受难的‘神之子’耶稣像前,这‘人之子’就受着裁判。”(卷4,第558—559页)他在一篇抗议官方压迫的文章中,曾宣布他曾收集过基督教历史上殉教者的材料,但他最喜爱的牺牲者形象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那段动人的话是值得再次引用的: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卷4,第209页)
这个普罗米修斯的隐喻原是用来为他的翻译辩护的,但言外之意更宽广。在许多方面,这是他的革命努力的一个概括。这里,革命者的形象(事实上也是他的自我形象)是一个深刻的悲剧形象,因为体现的最终意义就是牺牲。不仅是为公众殉难,也是内心的自我折磨。这个形象是他过去许多作品的回响。就这样,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又提出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吃人”问题,这次却是对他自己而说。
当年的狂人是自觉受到周围人的迫害,是害怕人们要吃自己,而普罗米修斯式的革命者却把“吃人”转向内面——煮自己的肉加以咬嚼也让人民咬嚼——使自己成为为人民牺牲的典范。这当然是一个高尚的救世者的形象。人们不免要想,鲁迅心目中那些“咬嚼者”是不是专指青年和孩子,而这些青年和孩子是否真能从他的牺牲中得到较多的好处。